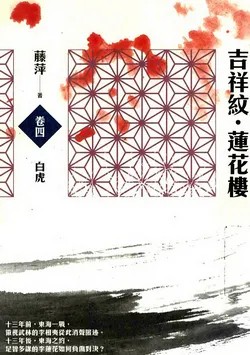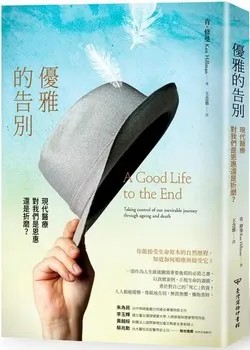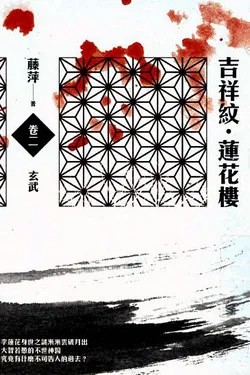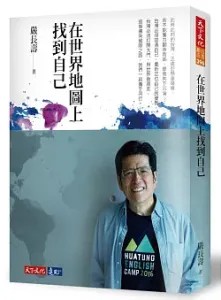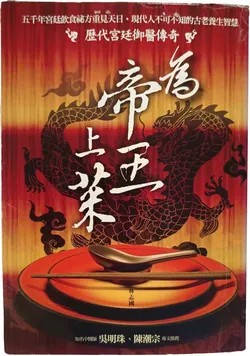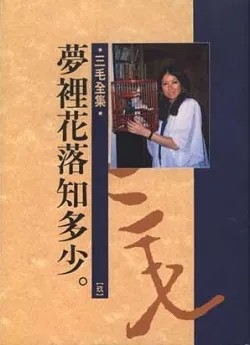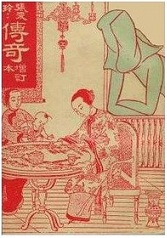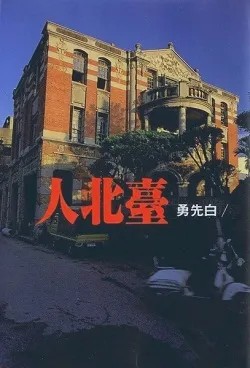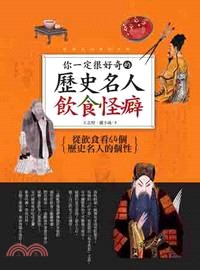搜尋好讀 - Google
404 無此網頁。好讀告示
Dear Haodoo Community,
After 25 years of serving you through Haodoo.net,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e launch of our new site: Haodoo.org!
As of July 1, 2025, all content created since November 2022 are now located on our brand-new platform at Haodoo.org. Built with the latest web technologies and powered by WordPress, the new site offers enhanced performance, improved navigation, and a more modern reading experience.
Haodoo.org hosts all newer content with faster loading times and better mobile compatibility.
Haodoo.net serves as an archive for the pre-2022 content.
We welcome you to explore Haodoo.org. Your continued support over the past 25 years has made this exciting upgrade possible.
Warm regards,
The Haodoo Team
好書更新 2026年2月
金庸【笑傲江湖】 第二十二章《脫困》劉小珍錄音 [1:31] 2026/2/28(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六篇《元明時代》第九章《河豚雖美味饕餮須謹慎》書亞錄音 [0:15] 2026/2/28(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二十一章《囚居》劉小珍錄音 [1:26] 2026/2/14(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六篇《元明時代》第八章《明朝宮廷飲食十二月》書亞錄音 [0:26] 2026/2/14(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六篇《元明時代》第七章「蟠龍菜」與「魚茸卷」》書亞錄音 [0:20] 2026/2/14(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二十章《入獄》劉小珍錄音 [1:47] 2026/2/7(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六篇《元明時代》第六章《美女紫蘇肉》書亞錄音 [0:15] 2026/2/7(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6年1月
金庸【笑傲江湖】 第十九章《打賭》劉小珍錄音 [1:56] 2026/1/24(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十八章《聯手》劉小珍錄音 [1:57] 2026/1/17(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六篇《元明時代》第五章《金陵鴨饌甲天下》書亞錄音 [0:22] 2026/1/17(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十七章《傾心》劉小珍錄音 [2:57] 2026/1/3(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六篇《元明時代》第四章《明太祖一生只有一個御廚》書亞錄音 [0:20] 2026/1/3(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12月
金庸【笑傲江湖】 第十六章《注血》劉小珍錄音 [1:31] 2025/12/20(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六篇《元明時代》第三章《御廚作業手冊---「飲膳正要」》書亞錄音 [0:16] 2025/12/20(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十五章《灌藥》劉小珍錄音 [1:31] 2025/12/6(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六篇《元明時代》第二章《元世祖「涮羊肉」》書亞錄音 [0:18] 2025/12/6(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11月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六篇《元明時代》第一章《蒙元大帝國的詐馬宴》書亞錄音 [0:32] 2025/11/29(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十四章《論杯》劉小珍錄音 [1:41] 2025/11/22(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五篇《遼宋時代》第十章《流向民間的「奇香燒鵝」與「護國菜」》書亞錄音 [0:17] 2025/11/22(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十三章《學琴》劉小珍錄音 [2:16] 2025/11/1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五篇《遼宋時代》第九章《孝宗趙昚的幾道「私家菜」》書亞錄音 [0:21] 2025/11/15(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十二章《圍攻》劉小珍錄音 [2:33] 2025/11/8(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五篇《遼宋時代》第八章《宋高宗戀上宋嫂魚羮》書亞錄音 [0:16] 2025/11/8(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五篇《遼宋時代》第七章《史上最奢華的一桌御宴菜單》書亞錄音 [0:26] 2025/11/1(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10月
金庸【笑傲江湖】 第十一章《聚氣》劉小珍錄音 [1:59] 2025/10/2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五篇《遼宋時代》第六章《宋徽宗的生日派對》書亞錄音 [0:16] 2025/10/2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五篇《遼宋時代》第五章《窮奢極欲的趙宋宮廷豪宴》書亞錄音 [0:22] 2025/10/18(有聲書籍)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十》景梅錄音 [0:39] 2025/10/11(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十章《傳劍》劉小珍錄音 [1:54] 2025/10/11(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五篇《遼宋時代》第四章《宋朝御宴的主打菜—燒羊肉》書亞錄音 [0:18] 2025/10/11(有聲書籍)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九》景梅錄音 [0:31] 2025/10/4(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九章《邀客》劉小珍錄音 [1:54] 2025/10/4(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五篇《遼宋時代》第三章《宋朝的御廚使是武官》書亞錄音 [0:24] 2025/10/4(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9月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八》景梅錄音 [0:35] 2025/9/27(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八章《面壁》劉小珍錄音 [2:11] 2025/9/27(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五篇《遼宋時代》第二章《遼代宮廷三大宴》書亞錄音 [0:25] 2025/9/27(有聲書籍)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七》景梅錄音 [0:53] 2025/9/20(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七章《授譜》劉小珍錄音 [2:06] 2025/9/20(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五篇《遼宋時代》第一章《御廚將遼太宗「羓」成「木乃伊」》書亞錄音 [0:18] 2025/9/20(有聲書籍)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六》景梅錄音 [0:48] 2025/9/13(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十一章《傳說中的“紅綾餅”與“紅虯脯”》書亞錄音 [0:14] 2025/9/13(有聲書籍)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五》景梅錄音 [0:54] 2025/9/6(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六章《洗手》劉小珍錄音 [1:26] 2025/9/6(有聲書籍)
倪匡【少年衛斯理】小瑜勘誤 2025/9/5(奇幻小說)
好書更新 2025年8月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四》景梅錄音 [1:07] 2025/8/30(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五章《治傷》劉小珍錄音 [2:42] 2025/8/30(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十章 《盛世御宴的招牌菜》書亞錄音 [0:28] 2025/8/30(有聲書籍)
Ruth Benedict【菊花與劍】KuoLiming勘誤 2025/8/28(歷史煙雲)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三》景梅錄音 [0:38] 2025/8/23(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四章《坐鬥》劉小珍錄音 [1:54] 2025/8/23(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九章《唐明皇誓將埋單進行到底》書亞錄音 [0:16] 2025/8/23(有聲書籍)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二》景梅錄音 [1:06] 2025/8/16(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八章《取締「燒尾宴」》書亞錄音 [0:21] 2025/8/16(有聲書籍)
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一》景梅錄音 [0:58] 2025/8/9(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三章《救難》劉小珍錄音 [2:01] 2025/8/9(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七章《武則天牌「蟲草全鴨」》書亞錄音 [0:15] 2025/8/9(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六章《「牡丹燕菜」的由來》書亞錄音 [0:15] 2025/8/2(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7月
金庸【笑傲江湖】 第二章《聆秘》劉小珍錄音 [2:00] 2025/7/26(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五章《「洛陽水席」名聞天下》書亞錄音 [0:13] 2025/7/19(有聲書籍)
金庸【笑傲江湖】 第一章《滅門》劉小珍錄音 [2:21] 2025/7/12(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20+21《不再視老化死亡為禁忌+下一步該往那走》景梅錄音 [0:29] 2025/7/12(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四章《釐清古代飲食界一樁打不完的官司》書亞錄音 [0:23] 2025/7/12(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8+19《如何選擇好醫師和好醫院+醫療化的悲歌》景梅錄音 [0:39] 2025/7/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三章《「渾羊殁忽」原是舶來品》書亞錄音 [0:16] 2025/7/5(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6月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四:白虎】 第三章《東海之約》劉小珍錄音 [1:10] 2025/6/28(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6+17《加護醫學-人生終點的起站+敲開天堂的門》景梅錄音 [0:40] 2025/6/28(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四:白虎】 第二章《血染少師劍》劉小珍錄音 [3:24] 2025/6/21(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4+15《學會放手+無效醫療》景梅錄音 [0:51] 2025/6/21(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二章《「金虀玉膾」與「蜜蟹」》書亞錄音 [0:19] 2025/6/21(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四:白虎】 第一章《紙生極樂塔》(下)劉小珍錄音 [3:51] 2025/6/14(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3《生前預囑》景梅錄音 [0:41] 2025/6/14(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一章《隋二世將美景變成美食》書亞錄音 [0:21] 2025/6/14(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四:白虎】 第一章《紙生極樂塔》(上)劉小珍錄音 [3:23] 2025/6/7(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1+12《衰弱症+善終不易》景梅錄音 [0:43] 2025/6/7(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十章《「鵝掌」誘得帝王心》書亞錄音 [0:21] 2025/6/7(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5月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0《診斷面臨的兩難》景梅錄音 [0:43] 2025/5/31(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九章《朕的國宴的素席》書亞錄音 [0:25] 2025/5/31(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三:青龍】 第四章《懸豬記》劉小珍錄音 [2:41] 2025/5/24(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8+9《丹尼絲的宣言+持續演進的加護醫學》景梅錄音 [0:42] 2025/5/24(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三:青龍】 第三章《饕餮銜首金簪》劉小珍錄音 [1:44] 2025/5/17(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7《認知能力衰退》景梅錄音 [0:30] 2025/5/17(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6《加護病房的現況》景梅錄音 [0:15] 2025/5/10(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八章《從羊羹到水盆羊肉》書亞錄音 [0:18] 2025/5/10(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三:青龍】 第二章《食狩村》劉小珍錄音 [3:20] 2025/5/3(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5《細胞凋亡》景梅錄音 [0:13] 2025/5/3(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七章 《問「粣」為何物》書亞錄音 [0:20] 2025/5/3(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4月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三:青龍】 第一章《龍王棺》劉小珍錄音 [3:00] 2025/4/26(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4《晚年跌倒》景梅錄音 [0:35] 2025/4/26(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六章《暴食起來不要命的「豬王」皇帝》書亞錄音 [0:17] 2025/4/26(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3《為搶救而搶救》景梅錄音 [0:22] 2025/4/19(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二:玄武】 第四章《繡花人皮》劉小珍錄音 [1:42] 2025/4/19(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五章《美味不過是「項臠」》書亞錄音 [0:14] 2025/4/19(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2《衰老是人生必經之途》景梅錄音 [0:59] 2025/4/12(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二:玄武】 第三章《女宅》劉小珍錄音 [1:47] 2025/4/12(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四章《黃瓜從此不姓「胡」》書亞錄音 [0:17] 2025/4/12(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我母親人生中的最後六個月》景梅錄音 [0:19] 2025/4/5(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二:玄武】 第二章《窟窿》劉小珍錄音 [2:16] 2025/4/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三章《帝王御宴的尷尬》書亞錄音 [0:22] 2025/4/5(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3月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0《作者+前言》景梅錄音 [0:16] 2025/3/29(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二章《「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書亞錄音 [0:19] 2025/3/29(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二:玄武】 第一章《觀音垂淚》劉小珍錄音 [5:01] 2025/3/22(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一章《麵食的名字來源於美男子的那張臉》書亞錄音 [0:19] 2025/3/22(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尾聲《我們除了彼此互愛,沒有別的選擇》景梅錄音 [0:11] 2025/3/15(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四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宗教的定位《4-2面對大佛最美的時刻》景梅錄音 [0:11] 2025/3/15(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四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宗教的定位《4-1大師消失,典範難尋》景梅錄音 [0:16] 2025/3/1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十一章《雞肋與鱸魚膾》書亞錄音 [0:24] 2025/3/15(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三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地方的定位《3-4留白。永續》景梅錄音 [0:15] 2025/3/8(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三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地方的定位《3-3美麗島嶼,綠能的想像》景梅錄音 [0:18] 2025/3/8(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三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地方的定位《3-2不老部落,永續的未來》景梅錄音 [0:14] 2025/3/8(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三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地方的定位《3-1池上,自在精彩》景梅錄音 [0:16] 2025/3/8(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十章《寂寞王朝並不寂寞》書亞錄音 [0:20] 2025/3/8(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二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台灣的定位《2-3危機,也是轉機》景梅錄音 [0:29] 2025/3/1(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二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台灣的定位《2-2伸出友誼手,把感動放前面》景梅錄音 [0:15] 2025/3/1(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二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台灣的定位《2-1不要用錯誤的尺度測量自己》景梅錄音 [0:17] 2025/3/1(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九章《最愛鮑魚的民選皇帝王莽》書亞錄音 [0:22] 2025/3/1(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2月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一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青年的定位《1-3創建台灣的 Minerva Schools》景梅錄音 [0:14] 2025/2/22(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一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青年的定位《1-2世界就是校園》景梅錄音 [0:14] 2025/2/22(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一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青年的定位《1-1科技浪潮下,青年的未來何在?》景梅錄音 [0:23] 2025/2/22(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前言《未來已經成為現在》景梅錄音 [0:18] 2025/2/22(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6《結論,不再惡夢》景梅錄音 [0:23]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5《什麼才能拯救鄉巴佬》景梅錄音 [0:32]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4《與內在的怪物戰鬥》景梅錄音 [0:30]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3《幸福的人擁有什麼》景梅錄音 [0:36]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2《耶魯法學院的異類》景梅錄音 [0:29]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1《絕望的白人與討厭Obama的理由》景梅錄音 [0:42]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0《海軍陸戰隊的日子》景梅錄音 [1:05]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9《姥姥的家》景梅錄音 [0:58]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8《狼養大的孩子》景梅錄音 [0:24]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7《最好的爸爸》景梅錄音 [0:42]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6《我的父親們》景梅錄音 [0:49]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5《人生最大的錯誤》景梅錄音 [0:54]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4《美夢難圓》景梅錄音 [0:36]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3《家庭至上》景梅錄音 [0:20]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2《離鄉背景》景梅錄音 [0:37]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傑克遜老家鄉》景梅錄音 [0:30]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0《作者簡介+一部荒謬的自傳》景梅錄音 [0:26] 2025/2/1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八章《南越王宴的酒與菜》書亞錄音 [0:19] 2025/2/1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七章《帝王中的廚神》書亞錄音 [0:14] 2025/2/8(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1月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六章 《關於「鱁鮧」的公案》書亞錄音 [0:19] 2025/1/2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五章 《隱士的美味佳餚上了帝王宴》書亞錄音 [0:17] 2025/1/2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四章《「鹿肚炙」原來是入夥飯的下酒菜》書亞錄音 [0:11] 2025/1/18(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三章 《漢劉邦與「黿汁狗肉」》書亞錄音 [0:20] 2025/1/18(有聲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