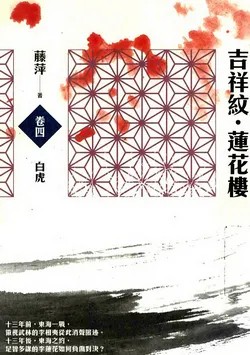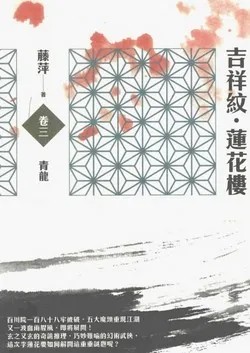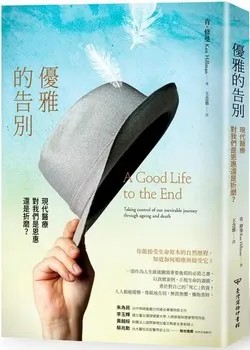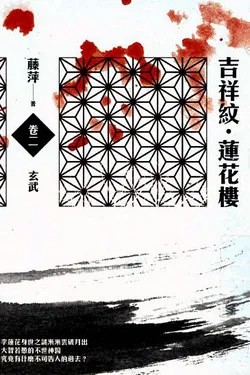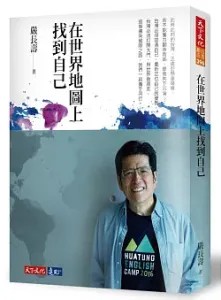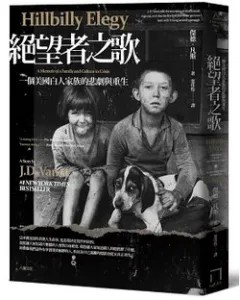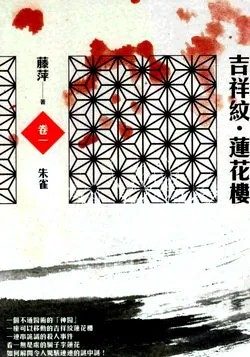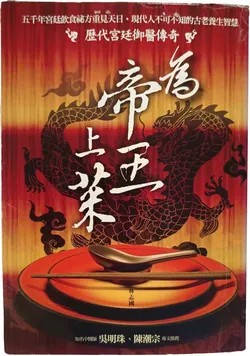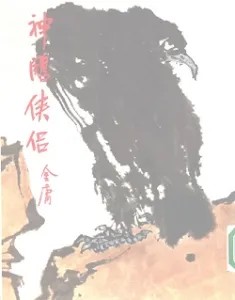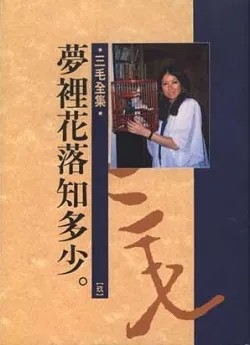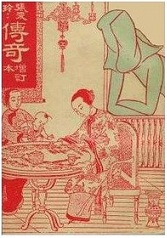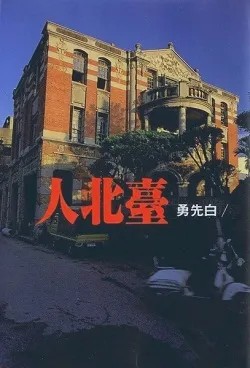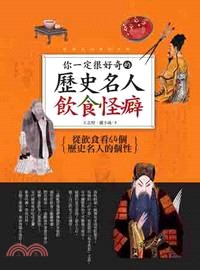搜尋好讀 - Google
404 無此網頁。好讀告示
Dear Haodoo Community,
After 25 years of serving you through Haodoo.net,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e launch of our new site: Haodoo.org!
As of July 1, 2025, all content created since November 2022 are now located on our brand-new platform at Haodoo.org. Built with the latest web technologies and powered by WordPress, the new site offers enhanced performance, improved navigation, and a more modern reading experience.
Haodoo.org hosts all newer content with faster loading times and better mobile compatibility.
Haodoo.net serves as an archive for the pre-2022 content.
We welcome you to explore Haodoo.org. Your continued support over the past 25 years has made this exciting upgrade possible.
Warm regards,
The Haodoo Team
好書更新 2025年7月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三章《「渾羊殁忽」原是舶來品》書亞錄音 [0:16] 2025/7/5(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6月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四:白虎】 第三章《東海之約》劉小珍錄音 [1:10] 2025/6/28(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6+17《加護醫學-人生終點的起站+敲開天堂的門》景梅錄音 [0:40] 2025/6/28(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四:白虎】 第二章《血染少師劍》劉小珍錄音 [3:24] 2025/6/21(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4+15《學會放手+無效醫療》景梅錄音 [0:51] 2025/6/21(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二章《「金虀玉膾」與「蜜蟹」》書亞錄音 [0:19] 2025/6/21(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四:白虎】 第一章《紙生極樂塔》(下)劉小珍錄音 [3:51] 2025/6/14(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3《生前預囑》景梅錄音 [0:41] 2025/6/14(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四篇《隋唐五代時代》第一章《隋二世將美景變成美食》書亞錄音 [0:21] 2025/6/14(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四:白虎】 第一章《紙生極樂塔》(上)劉小珍錄音 [3:23] 2025/6/7(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1+12《衰弱症+善終不易》景梅錄音 [0:43] 2025/6/7(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十章《「鵝掌」誘得帝王心》書亞錄音 [0:21] 2025/6/7(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5月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0《診斷面臨的兩難》景梅錄音 [0:43] 2025/5/31(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九章《朕的國宴的素席》書亞錄音 [0:25] 2025/5/31(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三:青龍】 第四章《懸豬記》劉小珍錄音 [2:41] 2025/5/24(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8+9《丹尼絲的宣言+持續演進的加護醫學》景梅錄音 [0:42] 2025/5/24(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三:青龍】 第三章《饕餮銜首金簪》劉小珍錄音 [1:44] 2025/5/17(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7《認知能力衰退》景梅錄音 [0:30] 2025/5/17(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6《加護病房的現況》景梅錄音 [0:15] 2025/5/10(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八章《從羊羹到水盆羊肉》書亞錄音 [0:18] 2025/5/10(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三:青龍】 第二章《食狩村》劉小珍錄音 [3:20] 2025/5/3(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5《細胞凋亡》景梅錄音 [0:13] 2025/5/3(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七章 《問「粣」為何物》書亞錄音 [0:20] 2025/5/3(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4月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三:青龍】 第一章《龍王棺》劉小珍錄音 [3:00] 2025/4/26(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4《晚年跌倒》景梅錄音 [0:35] 2025/4/26(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六章《暴食起來不要命的「豬王」皇帝》書亞錄音 [0:17] 2025/4/26(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3《為搶救而搶救》景梅錄音 [0:22] 2025/4/19(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二:玄武】 第四章《繡花人皮》劉小珍錄音 [1:42] 2025/4/19(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五章《美味不過是「項臠」》書亞錄音 [0:14] 2025/4/19(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2《衰老是人生必經之途》景梅錄音 [0:59] 2025/4/12(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二:玄武】 第三章《女宅》劉小珍錄音 [1:47] 2025/4/12(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四章《黃瓜從此不姓「胡」》書亞錄音 [0:17] 2025/4/12(有聲書籍)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1《我母親人生中的最後六個月》景梅錄音 [0:19] 2025/4/5(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二:玄武】 第二章《窟窿》劉小珍錄音 [2:16] 2025/4/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三章《帝王御宴的尷尬》書亞錄音 [0:22] 2025/4/5(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3月
肯・修曼《優雅的告別》 0《作者+前言》景梅錄音 [0:16] 2025/3/29(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二章《「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書亞錄音 [0:19] 2025/3/29(有聲書籍)
藤萍【吉祥紋蓮花樓卷二:玄武】 第一章《觀音垂淚》劉小珍錄音 [5:01] 2025/3/22(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三篇《魏晉南北朝時代》第一章《麵食的名字來源於美男子的那張臉》書亞錄音 [0:19] 2025/3/22(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尾聲《我們除了彼此互愛,沒有別的選擇》景梅錄音 [0:11] 2025/3/15(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四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宗教的定位《4-2面對大佛最美的時刻》景梅錄音 [0:11] 2025/3/15(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四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宗教的定位《4-1大師消失,典範難尋》景梅錄音 [0:16] 2025/3/1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十一章《雞肋與鱸魚膾》書亞錄音 [0:24] 2025/3/15(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三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地方的定位《3-4留白。永續》景梅錄音 [0:15] 2025/3/8(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三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地方的定位《3-3美麗島嶼,綠能的想像》景梅錄音 [0:18] 2025/3/8(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三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地方的定位《3-2不老部落,永續的未來》景梅錄音 [0:14] 2025/3/8(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三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地方的定位《3-1池上,自在精彩》景梅錄音 [0:16] 2025/3/8(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十章《寂寞王朝並不寂寞》書亞錄音 [0:20] 2025/3/8(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二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台灣的定位《2-3危機,也是轉機》景梅錄音 [0:29] 2025/3/1(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二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台灣的定位《2-2伸出友誼手,把感動放前面》景梅錄音 [0:15] 2025/3/1(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二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台灣的定位《2-1不要用錯誤的尺度測量自己》景梅錄音 [0:17] 2025/3/1(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九章《最愛鮑魚的民選皇帝王莽》書亞錄音 [0:22] 2025/3/1(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2月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一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青年的定位《1-3創建台灣的 Minerva Schools》景梅錄音 [0:14] 2025/2/22(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一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青年的定位《1-2世界就是校園》景梅錄音 [0:14] 2025/2/22(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第一章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青年的定位《1-1科技浪潮下,青年的未來何在?》景梅錄音 [0:23] 2025/2/22(有聲書籍)
嚴長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前言《未來已經成為現在》景梅錄音 [0:18] 2025/2/22(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6《結論,不再惡夢》景梅錄音 [0:23]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5《什麼才能拯救鄉巴佬》景梅錄音 [0:32]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4《與內在的怪物戰鬥》景梅錄音 [0:30]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3《幸福的人擁有什麼》景梅錄音 [0:36]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2《耶魯法學院的異類》景梅錄音 [0:29]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1《絕望的白人與討厭Obama的理由》景梅錄音 [0:42]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0《海軍陸戰隊的日子》景梅錄音 [1:05]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9《姥姥的家》景梅錄音 [0:58]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8《狼養大的孩子》景梅錄音 [0:24]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7《最好的爸爸》景梅錄音 [0:42]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6《我的父親們》景梅錄音 [0:49]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5《人生最大的錯誤》景梅錄音 [0:54]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4《美夢難圓》景梅錄音 [0:36]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3《家庭至上》景梅錄音 [0:20]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2《離鄉背景》景梅錄音 [0:37]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1《傑克遜老家鄉》景梅錄音 [0:30] 2025/2/15(有聲書籍)
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0《作者簡介+一部荒謬的自傳》景梅錄音 [0:26] 2025/2/1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八章《南越王宴的酒與菜》書亞錄音 [0:19] 2025/2/1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七章《帝王中的廚神》書亞錄音 [0:14] 2025/2/8(有聲書籍)
好書更新 2025年1月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六章 《關於「鱁鮧」的公案》書亞錄音 [0:19] 2025/1/2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五章 《隱士的美味佳餚上了帝王宴》書亞錄音 [0:17] 2025/1/25(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四章《「鹿肚炙」原來是入夥飯的下酒菜》書亞錄音 [0:11] 2025/1/18(有聲書籍)
林志國【為帝王上菜:歷代宮廷御醫傳奇】 第二篇《秦漢時代》第三章 《漢劉邦與「黿汁狗肉」》書亞錄音 [0:20] 2025/1/18(有聲書籍)